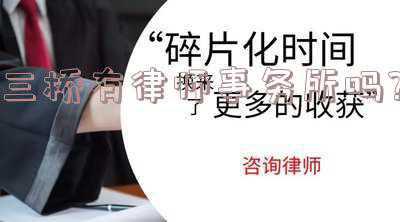三元桥附近律师事务所哪家好(“在大城市租套合适的房子太难了”)
其他 | 2023年06月16日 | 阅读:177 | 评论:2
“在大城市租到合适的房子太难了!”10月17日下午,29岁的刘源(化名)站在北京朝阳区花家地小区某单元楼前,一边清点行李,一边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刘源毕业两年多,已经搬了四次家。“房租太贵了。”他叹了口气。
目前,像刘源这样的刚需租房者不在少数。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将为3.76亿,其中相当一部分需要租房。不少受访者表示,在大城市租房面临着租房成本高、可选房源少、租房关系不稳定等问题,租房压力大。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这些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租赁住房市场供不应求的本质。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立法为住房租赁市场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必须增加租赁住房的供给。
房租占收入一半以上
频繁搬家,生活不稳定
毕业后,刘源在一家公司工作,通过某知名中介平台租了一间破房。房子虽然交通方便,离单位近,但是房租太贵。为了省钱,他后来找了个小中介租了个相对便宜的房间。
但租房的经历让他疲惫不堪:入住后发现房子卫生条件差,噪音大,但交了管理费和卫生费后却无人提供服务,与中介交涉时对方态度蛮横。最后,刘源只是通过拨打北京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追回了剩余的房租。
租房很多次,最让刘源接受不了的就是房租——一套“老小”,两个卧室一个小客厅,没有窗户,租其中一个小卧室居然要3000元到3500元,占了他月收入的一大半。“住得离公司近,房租贵得离谱;房租低的一般都在郊区,通勤是个问题。”
他还发现,无论通过哪个中介租房,最长租期都是一年。“合同到期后,按理说第二年续租应该免中介费,但实际上不仅有中介费要交,租金也有一定的上涨。我只能在合同到期前找到价格优惠的房子。”
对刘源来说,每一次换房都是一次挑战。“在有限的预算内找到一套相对满意的房子并不容易,看房、砍价、避坑等很多环节都不能马虎。”有一次,他一天看了四个小区的七套房,觉得筋疲力尽。
采访中,刘源预约的互联网搬家平台的货车冲到了单元楼前。刘源和司机把在北京的所有家当都装进车里,出发去新的租住地。
这次和同事合租了一套两居室,每月6200元。按照合同要求的“一送一、三送一”的付款方式及其他杂费,他们各付给中介1.5万元。对于几乎没有积蓄的刘源和同事来说,这笔钱“压力很大,我们都是借的钱”。
刘源的租房经历,33岁的林晓(化名)深有同感。10年前,她从河南老家到北京找工作,从此开始了租房的历史。因为收入低,她当时在国茂附近租了一套三室二厅,月租1500元。
“家乡的生活环境还不错。突然和这么多陌生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很不舒服。”林晓很快就搬出去了,一个人租了一套两居室。月租涨到4000元。很快,她意识到这样租房子“又贵又浪费”,只好在网络论坛上发帖,很快找到了一个女生合租。
平静的生活总是难以持久。2016年,房东临时通知她收回房子。无奈之下,林晓和室友赶紧通过中介平台租了一套两居室。但合同签订后不久,房主就把房子卖了,给他们两周时间搬出去。
“毕竟是人家的房子,我们也没太较真。还好房东当时给了我们一些补偿。”回顾10年的租房经历,林晓坦言告诉记者,“租房子,频繁搬家,感觉很没有安全感”。
申请保障性租赁房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通勤一点也不舒服
租金低又不用经常搬家的房子,住起来有很多不便。这是90后海归大师、某短视频平台博主郭邦邦的深切感受。
10月16日下午,记者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到了留着长发、穿着米色外套的她。“第一,不舒服;二是通勤时间长;第三,服务跟不上。”郭邦邦说,在北京西五环附近的公租房住了半年后,她和丈夫毅然搬了出来。
郭邦邦,29岁硕士,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她在学校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毕业后来到北京打拼。起初,夫妻俩在北京租房子住,月租7000元左右。
2020年初,她老公单位通知她可以申请人才公租房作为经济适用房。这对没有北京户口的夫妇试图申请,却意外申请到了一套零居室(全开间)公租房。
“我们申请的时候,看着别人申请的两居室、三居室竞争激烈,就选择了反方向的小户型,这样申请的几率更大。”郭邦邦说,当年9月,他们搬进了公租房,月租2000多元。房租突然降了很多,感觉还挺好的。
但郭邦邦很快就发现了房子的“坏处”:房间面积太小,放不下一张大床,在空里也没剩多少空间。有一次做饭把房间弄得满满的,我上厕所的时候转身撞到了头。郭邦邦的老公经常在云上开会。为了不打扰丈夫工作,她要么出去散步,要么呆在厕所里。
“当时我俩都觉得生活质量直线下降,很难受,甚至有些抑郁。”她说,另外,通勤太远也是个大问题。她在CBD上班,每次坐公交都要一个半小时,尤其是从八宝山地铁站出来,逆风往回走。冬天北风吹,路上人少,紧挨着墓地,她“又累又怕”。
周边配套生活设施也不足。菜市场和超市都比较远,购物特别不方便;有一次,她晚上下班回家,发现指纹锁打不开了。她电话联系管理员,找不到人,一下子也找不到开锁师傅。她不得不在门口等了大半天。
有时候她会想:“为什么你要为这个小房子这么努力呢?”
2020年底,丈夫从原单位辞职,公司申请了人才公租房。离职意味着放弃人才济济的公租房。今年1月,夫妻俩搬出公租房,在北京三元桥附近租了一套房。租房的烦恼还在继续。
租赁市场有待填补的缺陷
住房供需矛盾必须解决
像郭邦邦、刘源这样需要租房、为租房而烦恼的人不在少数。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流动人口的扩大,年轻人的住房困难日益突出。去年9月发布的《2020中国青年租房生活蓝皮书》称,城市租房生活已成为超2亿人的选择。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房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秀池长期关注住房问题。她告诉记者,房屋租赁市场是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各城市的住房短缺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以新市民和无房青年为主。短期内主要通过租房解决住房问题。因此,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重点是发展和规范租赁市场。
“解决这些人的住房问题,要租售并举,尽力解决新市民的住房困难。”北京市物权法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毕说。
对于如何解决租房群体遇到的租房成本高、可选房源少、租房关系不稳定、纠纷解决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专家们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毕认为,目前住房租赁市场存在一些混乱现象,反映出住房租赁市场的一些弊端,如市场秩序规范缺失,部分房产中介发布虚假房源信息,不退押金房租,恶意驱逐租客,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等。
“在一定程度上,监管体制和机制处于缺位状态。各部门信息不够通畅,各自为政。没有建立相关的联合监管机制。多头执法和盲目执法并存。”毕文强指出。
在赵秀池看来,当前住房租赁市场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因为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各地各部门一直以产权房销售为主,对租赁市场关注较少。
北京大学法学院房地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楼建波表示,问题的背后反映了我国租赁住房的供需矛盾。无论是市场化的租赁房还是保障性租赁房,普遍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目前,租赁市场存在结构性问题。从权利义务来看,承租人在信息知识、交易状态、交易形式等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就需要从法律上进一步保护租房者的权益。”毕·文强说。
增加供给以平衡供需
完善制度的特别立法
林萧一直“渴望住在自己的房子里”。租住期间,她申请购买了共有产权房,并于今年获得了购房资格。虽然离市区有点远,但她毕竟可以正式告别租房生活了。
“一两年后,直到住进自己的房子,我才会真正对这个城市有归属感。”林晓坦言。
郭邦邦也在买房路上。她和她丈夫正在努力省钱。他们打算这两年在北京四环买一套二手房,避免通勤。
以后刘源还得靠租房子住。他的希望是:“此举能让我活得更久,少一点租房的烦恼。感谢上帝。”
刘源的期望代表了许多租房者的心声。
那么,如何才能让租房者有一个稳定的预期,在城市里买得起,住得好?
在赵秀池看来,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的政府,应该为不同的收入群体提供不同的租赁住房。给低收入者提供经济适用房是政府的责任,中高收入者可以租商品房。
“发展租赁市场的一项长期政策是出台住房租赁条例,以保证双方稳定的租赁关系。市场更多的是市场行为,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政府可以负责低端安全。”赵秀池表示,个人租赁仍是租赁市场的主力军,也能让租客“买得起,住得好”。降低租赁住房交易成本和租客负担,对增加供给、稳定租赁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毕文强的建议是提高有效供给。“新市民和年轻人长期居住的住房是交通区位便利、价格低端、面积小的租赁住房;是租赁关系稳定、纠纷容易解决的出租屋;是能满足基本居住需求的保障性租赁房。”
楼建波还建议增加租赁住房的供应。政府不仅要加大保障性、政策性租赁资源的供给,还要设计相关制度,鼓励产权人将闲置资源投入租赁住房市场,使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在楼建波看来,这个制度必须能够公平公正地保护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利益。比如,鼓励建立中长期租赁制度,允许出租人每年合理提高租金,稳定租赁关系。
“在住房租赁市场中,只有供求关系达到基本平衡,才能制定完善、公正、规范的制度,以专门立法为住房租赁市场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楼建波说。
(法治日报)
本文标签: 三桥有律师事务所吗?
温馨提示:本文是作者 小白测评 发表的文章,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相关文章
红际法律
- 最近发表
- 推荐文章
-
- 房屋装修合同范本2019(房屋装修合同样本怎么写?房屋装修的具体流程?)
- 合同专用章有编号吗(注意!漯河老俩口被骗)
- 合同专用章需要备案吗(2022年办理刻章备案都需要什么材料?)
- 合同专用章样式(最高法院民二庭:关于四个公章实务问题的解答)
- 合同专用章图片(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法人章,各印章的功能及注意事项)
- 合同专用章和公章的区别(财务章、公章、合同章、发票章,有关印章的最全风险汇总)
- 合同专用章尺寸大小(行政管理:企业印章管理暂行细则(中小企业适用))
- 合同专用章电子章制作(「放心签」合同电子签章怎么弄)
- 房屋装修合同简单范本(房屋装修施工合同范本)
- 房屋装修合同范本2021(房屋装修合同(简单)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