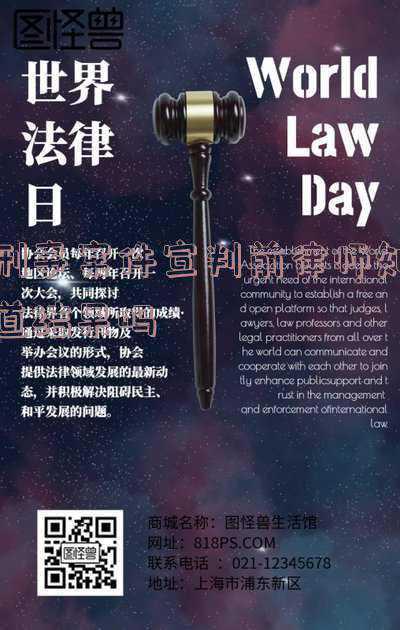律师会不会提前知道判决结果(实务中认罪认罚制度的畸变及律师辩护策略(中))
其他 | 2023年06月16日 | 阅读:315 | 评论:1
作者:熊成兴律师
作者简介:华中科技大学法学硕士,专职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广州黄埔法院特邀调解员,中国微信诗歌学会会员,湖北省诗歌学会会员。
点击最后一部分:认罪认罚制度在实践中的扭曲与律师的辩护策略(一)
02。被告人认罪后意味着什么?如果在实践中所有的基层检察院和法院都能按照陈国庆副检察长和杨立新审判长的回答来执行,那么认罪认罚制度的“是”与“应然”之间的差距就可以无限缩小。然而现实是,“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总是有巨大的差距。美好的制度设计一旦付诸实践,总会变味走样。在我看来,认罪认罚制度在实践中有时被扭曲成了一种博弈,是被告人与检察院和法院、律师与被告人、律师与检察院和法院的三方博弈。
在讨论这个变形游戏之前,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问题:认罪从宽制度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主要是诉讼经济,节约司法资源。根据《关于认罪认罚从宽的指导意见》开头写的一段话,“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准确及时惩治犯罪,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促进繁简刑事案件分流,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一般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的刑事案件,都会采用简易程序甚至速裁程序审理,快捷高效,检察院、法院和律师的工作量大大减轻。民事诉讼领域的调解制度也有类似的性质,所以在实践中,基层法院都会追求“撤诉率”这一指标。在刑事诉讼中,一些检察院甚至有所谓的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率指标。
其次,被告人的“认罪认罚”本身具有补充和强化案件证据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的定罪证据。“认罪认罚”要求被告人承认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犯罪事实的认定需要证据相互印证。《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有罪,不予处罚。”因此,在刑事案件中只有被害人陈述的实质证据(即被告人实施了犯罪行为)时,被告人本人是否认罪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这种被告人的“认罪认罚”,起着定罪证据的关键作用,在性犯罪中较为常见。对于其他刑事案件,公安机关通常根据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来收集其他证据,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往往对公安破案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这就是“举证在先”。当然,如果案件证据充分,被告人认罪与否根本不影响定罪量刑(也称“零口供”),那么被告人认罪自罚的意义就在于争取可以从轻处罚的情节。
第三,被告人为了给自己争取从轻处罚而“认罪认罚”。【/s2/】如前所述,在定案证据(包括定罪量刑证据)已经充分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般会如实认罪,甚至愿意在公安侦查阶段认罪并接受处罚。
以上三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是基于司法制度的宏观视角,第二个是基于办案机关判决的视角,第三个是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趋利避害”的功利视角。第一条没什么好说的,但是第二条和第三条在实际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很容易转化为博弈(也就是我上面说的,被告人与检察院和法院,律师与被告人,律师与检察院和法院的三重博弈)。
先来看第一款重度游戏[/s2/]。比如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可以作为定案的关键证据。因为被告人在公安侦查阶段往往不知道公安掌握了哪些证据,所以一开始可能不会认罪。但案件移送检察院后,当检察官告诉他如果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时,特别是当检察官坚定、强烈地认为立案证据足以认定其构成一定犯罪时,律师也会在会上告知犯罪嫌疑人这种风险。但有时在这类案件中,从辩护律师的角度来看,被告人可能根本不构成被指控的犯罪(比如定罪证据根本不符合“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但公安机关、检察院坚信证据充分(比如我代理过的两起强奸案,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公安机关、检察院均适用“优势证据”标准认定被告人犯强奸罪,一审法院均判决被告人有罪。 这时,被告人可能会逐渐产生心理动摇,开始相信律师能够成功地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即使律师夸大了自己的辩护观点和想法。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检察院和法院之间就形成了第一次博弈:虽然律师想坚持无罪抗辩,但是被告人的眼睛看着检察院的态度那么坚定,如果不认罪不处罚,检察院可能会给出更重的量刑建议,法院可能会完全采纳检察院的意见,这种可能性看起来挺大的。对于事实有争议的刑事案件,这种博弈未必容易出现。比如,如果被告人没有实施犯罪事实,可以自始至终不认罪。但是,对于那些法律适用有争议或案情复杂的案件,被告完全有可能在含糊不清之间最终达成妥协。就像我上面举的例子,被告的心理防线已经被“突破”。
第二个博弈是律师和被告之间的博弈。被告花钱请律师辩护的目的是希望律师尽可能为自己争取最好的结果。从律师的角度来说,接受委托后,任何一个认为该案有无罪抗辩空的律师,都想把它变成一个经典的无罪案件。所以律师倾向于无罪辩护。但是,一旦出现上述第一种博弈,律师与委托人(被告人)之间也会出现一种无形的博弈:如果委托人坚持无罪辩护,那么律师可以毫无顾忌地发表无罪辩护意见就很容易了;而当被告人的心理防线出现松动甚至“突破”时,此时,当事人对律师并不十分信任(即当事人认为律师为自己争取无罪结果的可能性不大)。律师会继续鼓励、说服当事人坚持无罪辩护还是让其认罪,按照当事人意愿从轻处罚?认罪认罚,律师可能心理不愿意,认为委托人心理太脆弱,认罪认罚后往往无法再次不认罪,只能在量刑部分发表一些笼统的意见(我们都知道,一旦被告人认罪认罚,如果检察院给出具体的量刑建议,法院不采纳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的概率有多大?从大数据统计的角度来看,有百分之几可能不被采纳?相信很多律师对此深有感触)。如果对处罚不认罪,律师担心法院的判决结果与预期相差太远(比如法院完全支持检察院的观点),那么责任律师就脱不了干系。这第二场我深有体会。我曾经代理过一个故意伤害的案子,被告是女性,受害人是男性。案发时,被告人已经怀孕,即将分娩,所以当时公安直接取保候审。在检察院阶段(孩子一岁多的时候),检察官提前联系当事人,询问其是否认罪接受处罚。如果不认罪,检察院不会给他续保,可能会采取逮捕措施。但是那个案件是否构成正当防卫争议很大,我从公安阶段就一直坚持无罪辩护意见。但最终迫于检察院的压力,当事人签署了认罪悔罪书,办理了续保手续。后来可想而知,检察院不让律师做无罪辩护,一审判决后当事人也没有上诉(缓刑,当事人也接受了,毕竟不用去监狱服刑)。
第三个博弈是律师、检察院、法院之间的博弈。从逻辑上来说,这个第三个博弈源于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博弈,因为从律师的角度来说,刑事案件最终辩护的成败并不会给律师带来立竿见影的利益分歧,律师往往更担心自己辩护的结果会影响到当事人的最终判罚。但是,当事人本身并不精通法律。律师只能针对是否认罪以及认罪后可能出现的结果,给当事人分析相应的法律风险。有时候,当事人没有自己的意见,只让律师出主意。这时这个第三个博弈就产生了:如果当事人认罪接受处罚,对于非重大复杂案件,检察院往往会直接给出具体的量刑建议。从司法实践中的大数据统计来看,法院往往会采纳检察院的量刑建议。尤其是在被告人认罪并接受处罚后,检察院和法院不允许律师进行无罪辩护的情况下,律师会纠结于这个案子。如果建议当事人认罪接受处罚,结果基本可以提前预知。而且一审法院判决后,如果当事人上诉,检察院可以抗诉,二审法院可以突破“上诉不加刑”原则,对当事人从重处罚。如果建议当事人不认罪从轻处罚,律师可能会对自己的辩护思路和意见有信心,但一旦结合刑事诉讼实践,恐怕律师会对自己产生怀疑(即从法律上讲,律师是有信心不认罪的,但回到现实层面,法院可能大概率不会相信他们的意见)。
虽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辩诉交易制度,但它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和交易(陈国庆副检察长在采访中也做出了类似的表述)。被告人认罪悔罪后,获得一定程度的从轻处罚;但某种程度上,放弃可能是二审上诉获得改判的权利(也可以理解为“后悔权”的放弃)。所谓的“认罪认罚从宽”是基于什么样的从宽标准?应当基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据裁判”原则,也就是说,是与“应当如何”(即被告人本应如何定罪量刑)相比较后的宽大处理。所谓“辩不清”,只有在控辩双方在案件的定罪量刑等方面充分“对质”和“辩”对方的基础上,被告人的辩护权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案件的最终判决才更有可能符合实质正义。但一旦被告人认罪从轻处罚,如果不允许辩护律师不认罪,审判程序就会简化(速裁程序更正规),律师辩护空就会受到进一步挤压。(事实上,审判程序简化后,法官不会像普通被告不认罪那样仔细审查案件的每一个细节。某种程度上,对于认罪认罚的案件,法官往往不会花太多精力在案件的审理上)
这三种博弈的背后,其根源都是“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能不能做无罪辩护?”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在被告人认罪从轻处罚后,允许律师进行无罪辩护,这三重博弈自然都可以消除。
(未完待续...)
文/熊成兴,律师,中国法学会会员,广州黄埔法院特邀调解员。
本文标签: 刑事案件宣判前律师知道结果吗
温馨提示:本文是作者 艺术空间 发表的文章,不代表本站观点!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相关文章
红际法律
- 最近发表
- 推荐文章
-
- 房屋装修合同范本2019(房屋装修合同样本怎么写?房屋装修的具体流程?)
- 合同专用章有编号吗(注意!漯河老俩口被骗)
- 合同专用章需要备案吗(2022年办理刻章备案都需要什么材料?)
- 合同专用章样式(最高法院民二庭:关于四个公章实务问题的解答)
- 合同专用章图片(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法人章,各印章的功能及注意事项)
- 合同专用章和公章的区别(财务章、公章、合同章、发票章,有关印章的最全风险汇总)
- 合同专用章尺寸大小(行政管理:企业印章管理暂行细则(中小企业适用))
- 合同专用章电子章制作(「放心签」合同电子签章怎么弄)
- 房屋装修合同简单范本(房屋装修施工合同范本)
- 房屋装修合同范本2021(房屋装修合同(简单)模板)
-
-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