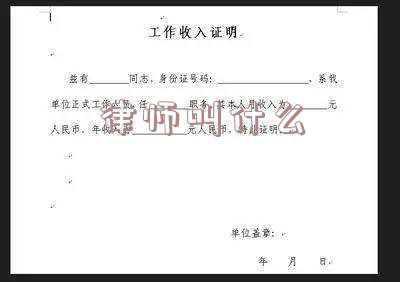古代律师叫什么(古代法律解释方法的变革与完善——以汉唐律学发展为视角)
其他 | 2023年06月16日 | 阅读:168 | 评论:1
法律解释与中国古代法学
所谓法律解释,是指对法律的含义、概念和术语进行进一步解释和说明的活动。我国现代法学理论中的法律方法论研究概括了广义的法律解释方法,主要包括文义解释、系统解释、客观解释、历史解释和社会学解释。
法律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按照一定的思想和观念对成文法律进行讲授、研究和注释的知识。据说它起源于春秋末期邓的《竹刑》,兴盛于《张都禄法》,成为对《唐律》的评论。因此,法律解释虽然是一个现代法律概念,但就其研究内容和方法而言,它不是舶来品,也不是近代以后才产生的。
早在秦代,中央司法机关颁布的秦简法律问答,就以问答或案例解释的形式,回答和解释了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法律术语和疑难问题,可以说是典型的官方法律解释文书。
晋代法学家杜预对法律解释的目标也做了非常准确的概括:“法家之书,非穷尽之书。所以文字直白,省听后切忌简单。例子很容易看到,禁止简单,但很难承诺。易见则人避,难犯则不及刑。”即找出法律规范的内在合理性,使一般的、抽象的法律条文易于理解、易于遵守、易于实施,从而达到立法者预设的各种目的。
唐代汉法发展综述
如果说秦简《答问答法》为中国古代法律的官方注释提供了早期样本的话,那么汉代春秋时期的审判则第一次将法学研究推向了历史高潮,诞生了中国古代早期的儒家法律学者。西汉武帝深受董仲舒倡导的理学影响,对法家之法进行了全方位的儒家化改造,要求在司法审判中,引用儒家经典分析案情、认定罪行,依据儒家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甚至优于成文法。从此,中国古代法律儒学化的历史进程也开始了,并对后来的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法学研究者把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注释法学。在法学诠释的理念上,秉承《晋律》中“简事”的法律思想,主张立法应简单明了,使人避之不及,为法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现实条件和丰富的理论材料,极大地促进了法学职业教育的繁荣。典型代表是张飞、杜预等“取汉代律师之功”,注解晋律。
《唐律亦舒》集汉晋法学研究之大成,继续秉承“绘一制,简而易从,立则约法,疏而不漏”的法律原则,准确阐释了唐律的立法精神和制度,完美展现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为政教之用”的特点。它还强调理解和文字的流畅,不仅成为各级司法官员分析法律和适用法律的依据。
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法理学思想和理论体系虽然存在差异,但都在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展和演变,即试图明确立法意图,区分法理学,明确法律条款和原则,用有限的法律条文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从而为中国法律制度的最终完善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为后世法理学及其解释技术的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方法论变革与理论完善
解释原则:从主观随意到客观理性。
汉代经学释法的核心原则是“本心”。韩《论盐铁刑》总结为:“《春秋》治狱,定罪以心为据。善而犯法者免,恶而顺法者罚。”即任何符合《春秋》精神的行为,即使违法,也不认为是犯罪。凡是不符合或违背《春秋》精神的,即使不违法也可以定罪。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由于过分强调主观动机,具有随意性。汉武帝时期的重臣宜颜以“屈尊罪”被判死刑,是对这种“原罪”的滥用。
《张度陆定律》是从成文法本身的立法原则出发对法律文本的注释,特别注重对法律原则和术语的解释。《杜金编年史》记载:“今笔记皆法意,以名命名。用户持名例判趣宅,绷绳墨迹直,析薪原理。”即探讨法律的精神实质,明确概念,便于执法者根据名、例、法的原则定罪议刑。而张飞则准确地定义和区分了“原因”、“损失”、“过失”、“欺诈”等20个近似罪名,为法律词汇的规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概念分析的方法明显不同于汉代的经学诠释,使法律的适用更加客观理性,不再过分受制于司法人员的主观意志和思想。
解释系统:从随机性和分散性到逻辑性和整体性。
法律解释的系统化是古代法学科学演进的重要标志。春判狱是一种临时性的、随意性的解释,即当具体事实出现或法律适用出现分歧时,就援引司法来讨论犯罪,从而呈现出零散、分散的特点。另一方面,虽然法学研究者大多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如舒、郭凌青、郑玄等。),而且他们对法律的解释具有权威性,甚至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指导,他们往往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的解释,甚至相互矛盾,这在实践中造成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金的法理学摆脱了经学和义理的束缚,遵循整体性、整体性的解释理念,形成了大量具有完整体系和结构的法理学著作。比如张飞写的《汉晋律序》和《杂律释文二十一卷》作为《泰初律注》,其中有很多类似的罪名,还有对立法原则和法律文本逻辑结构的理解,有些与现代刑法理论非常接近。《唐律亦舒》继承了魏晋时期法律注释的基本方法,即把法律文本和法律意义分章节,以句释词。附法律正文共502条,分12条30卷,使法律正文结构和文本风格更加完整成熟,更加具体、全面、准确、和谐。因为是官方注释法,所以在法律适用上也可以直接引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注释法典。
解释技术:从单一、被动到多元、主动
从春秋审判到唐律解释,在解释技术上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法”(儒家经典)对成文法的解释是事后的、被动的解释,而后者是从立法意图、历史渊源、文本结构等方面的综合解释。因此,它更关注法律条文的本体,是一种事前的、主动的解释。
另一方面,《唐律》更加完善,集中了历代法律注释的成果,吸取了众多学者的长处,引经据典,运用各种方法逐句解释法律。最典型的是历史解释,这种解释渗透着历史分析方法,从法律各章节、文本的来源,到条文中某一段的历史形成,让司法者了解法律的演变和变化过程。此外,还有类比解释。比如针对明安“罪无定法”的处理,引入“举重而轻”和“举轻而轻”的类比,尽可能涵盖各类犯罪,避免遗漏或有罪不罚。此外,更有目的的解释,有限的解释,扩大的解释等。
上述法律注释方法的运用,使“法疏”真正起到了解除法意、澄清法理、弥补法律不足的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法学的巅峰之作。
法学研究应不断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
中国古代法学经历了两千年的发展,虽然也有曲折和偶尔的衰落。但从历史客观性和全局来看,它始终以儒家思想与传统礼法的关系为主线,向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发展演变。汉代的法治开启了儒家法律的历史进程。金代注释法使法律解释不再受抽象的经义论束缚,实现了“以法解”的本体论回归和解释方法的科学转型。另一方面,《唐律亦舒》以其全面性和先进性著称,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注释的最高水平。宋代法制虽完善,但法理学成就略有下降。到了清代,法学研究迎来了新的繁荣,在应用法学、法制史、比较法、古代法律考证等领域成就突出。一批法学经典著作相继问世,如的《读法》、沈的《大清法注》、吴坦的《清代法规通考》、薛的《读法于疑》等,成为汉晋唐以后的主要著作。
从内在动因来看,中国古代社会深厚的成文法传统是法理学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历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是法理学研究不断进步的动力。他们熟读古代圣贤的教诲,依靠道德修养和对主流思想的深刻理解,弥补法律适用上的疏漏,最终实现法律思想的传承和永续。但是,只有顺应法学严谨性、逻辑性、系统性的本质,不断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植根于本土文化传统,进行理性、科学的改造和完善,法学研究才能具有更强的生命力。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人民法院)(寇)
(人民法院)
相关文章
红际法律
- 最近发表
- 推荐文章
-
- 房屋装修合同范本2019(房屋装修合同样本怎么写?房屋装修的具体流程?)
- 合同专用章有编号吗(注意!漯河老俩口被骗)
- 合同专用章需要备案吗(2022年办理刻章备案都需要什么材料?)
- 合同专用章样式(最高法院民二庭:关于四个公章实务问题的解答)
- 合同专用章图片(公章、财务章、合同章、发票章、法人章,各印章的功能及注意事项)
- 合同专用章和公章的区别(财务章、公章、合同章、发票章,有关印章的最全风险汇总)
- 合同专用章尺寸大小(行政管理:企业印章管理暂行细则(中小企业适用))
- 合同专用章电子章制作(「放心签」合同电子签章怎么弄)
- 房屋装修合同简单范本(房屋装修施工合同范本)
- 房屋装修合同范本2021(房屋装修合同(简单)模板)